正是由於「詩家語」有別於一般的文字,所以更促成了可以順著讀,亦能逆著讀的「回文詩」,乃至於將詩寫作環狀,並任意從中揀選一個字,無論順向、逆向都能讀的「字字回文詩」。

如《江南集》一書所錄〈織錦圖上回文原詩三首〉就曾寫道:
「紅手素絲千字錦,故人新曲九回腸。風吹絮雪愁縈骨,淚灑縑書恨見郎。」
這組詩的作者無法確定,但「織錦圖」乃源自五胡十六國時期蘇蕙之故實,因其思念丈夫竇滔,而將回文詩編織在錦緞上寄給遠方的丈夫。
故於字裡行間,彷彿見到了蘇蕙以白色絲線編織著回文詩的場景,蘇蕙不禁回憶起當年歡歌共伴的美好,於是備感哀傷而日漸消瘦,淚水濡濕了錦緞,恨不得能立即與丈夫相見。
逆著讀,則哀傷的心緒依舊,不過意思卻有所不同:
「郎見恨書縑灑淚,骨縈愁雪絮吹風。腸回九曲新人故,錦字千絲素手紅。」
呈現的是竇滔收到錦緞之後的情景,竇滔感受到了妻子恨不得相見的悲愁而淚落漣漣,身形也因思念而消瘦,一想到當年的新嫁娘如今亦已芳華不再,便哀傷不已,只能憑藉手中的錦緞睹物思人,恍惚間,似乎見到了妻子以纖纖素手編織出那一縷縷的萬千愁緒。
也就在順讀、逆讀之間,詞性的轉換、意思的改變,敘寫出了夫妻遙相思念的眷戀深情。
只是由於回文一類創作的遊戲性偏強,每每過於刻意,而有炫才、炫技之嫌,所以無論是鑑賞還是創作,好詩並不意味著就得像回文乃至藏頭一類創作炫才、炫技,關鍵理應在於能否適切地靈活運用各類手法體現個人情志。
具體情況仍得具體分析!
多元的修辭手法,如通感、譬喻、誇飾、雙關、藏詞、象徵、類疊、對偶、排比、層遞、頂真、鑲嵌、互文、仿擬、引用等,也是成就古典詩能展現「多重含意」的不同方式。惟有適切地靈活運用,才能情感飽滿、敘述生動而文理自然。亦即法不是死法,必須視情況變通活用,更不可以喧賓奪主,讓修辭手法以眩人耳目的姿態遮掩了主體情志。
不妨以晉代女子子夜所作〈子夜歌四十二首〉為例
這組詩大抵皆藉以表達對所愛之人的深切想望,其中有一首如此寫道:
「憐歡好情懷,移居作鄉里。桐樹生門前,出入見梧子。」
可以看到子夜對所愛之人傾心不已,故而遷居至同一鄉里,似乎能見到同一棵桐樹乃至散落一地的果實,便深感心滿意足。
但因「梧子」又與「吾子」諧音,所以這首詩還隱含有能不時遇見所愛之人的含意。
另外還有一首說:
「始欲識郎時,兩心望如一。理絲入殘機,何悟不成匹。」
表達出了子夜對完滿愛情的嚮往,只是愛情路上磕磕絆絆,遂以總織不好布體現出內心的哀傷。不過也由於「絲」與「思」諧音,「匹」又有匹配佳偶之義,因此這首詩還有思戀不已,卻無法與所愛之人走到一處的心不甘、情不願。
又如唐人李白的〈灞陵行送別〉一詩
這一年春天是李白來到京城的第三個年頭,在送王姓友人離京時寫下了這首詩,其中有云:
「我向秦人問路岐,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。古道連綿走西京,紫闕落日浮雲生。」
由於眼前有條岔路,李白便向在地人詢問這條岔路的去向,得知這條岔路是漢末李傕、郭汜禍亂長安之際, 王粲離京並於途中寫下「南登灞陵岸,迴首望長安」之詩句的通道,因以彰顯此時此刻與離京友人分別的氛圍。
只是李白筆下那「古道」二字在「頂真」手法的呈現中,顯得格外醒目。
事實上,李白是結合道路可供雙向通行的特性,凸顯這條通道是「邁向」或「遠離」政治權力核心的途徑,尤其友人的離京,也激起了李白心中的漣漪,三年前滿懷欣喜地進京,卻始終都未能獲得君王重用,暗地裡遂亦萌生離京的念頭,所以才會接著感慨道:「古道連綿走西京,紫闕落日浮雲生。」表示這是一條邁向理想的道路,無奈那像浮雲一般地小人,竟障蔽了象徵君王的太陽,那麼,恐怕也就只能選擇踏上歸途了!
至春夏之交,李白便離開京城了。一首送別之作,李白巧妙地運用了道路的特性,賦予「邁向」或「遠離」理想的象徵內涵,從而寄寓個人懷抱。

還有杜甫的〈别房太尉墓〉一詩
房琯是一位對杜甫有知遇之恩的高官,後於四川一地病故,而在房琯過世後的第二年,由於杜甫要離開四川,便特意前往房琯墓前與之告別,並寫下了這首詩。
其中可以看到「對棋陪謝傅,把劍覓徐君」一語,連用兩個歷史典故:
「對棋陪謝傅」是謝安在和姪子謝玄下棋時,謝安曾轉頭告訴外甥羊曇,不僅會取勝,並且還將轉贈贏來的大獎(一幢別墅)給羊曇。
「把劍覓徐君」乃徐君十分衷愛季札的佩劍,但因季札公務在身,一時無法相贈,等到公務執行完畢,季札特意前往拜訪徐君,不料徐君竟已過世,季札便解下佩劍掛在墳樹上。
兩個歷史典故充分體現出了深切的情誼,只是杜甫對典故的運用十分細緻:
謝安對羊曇的關愛,表現的是房琯對杜甫的青睞;季札對徐君的餽贈,表現的則是杜甫對房琯的感念之情,就好比此刻站在墓前的杜甫,儘管沒有贈劍之舉,但卻可以感受到杜甫那發自內心地真情實意。
而清末臺灣仕紳丘逢甲的〈元夕無月〉這組詩
丘逢甲在乙未割臺後,號召全島仕紳、軍民奮勇抗日,隨著日軍節節進逼,眼見時勢已無可為,不得已內渡廣東。
也就在三年之後的元宵佳節,思鄉心切的丘逢甲只能隔海遠眺而寫下這組詩,全詩由五首七言絕句所構成,均採用「頂真」的修辭手法,並扣緊深具團圓美好之象徵意義的元宵月,使之成為一組結構完整而充滿家國之思的組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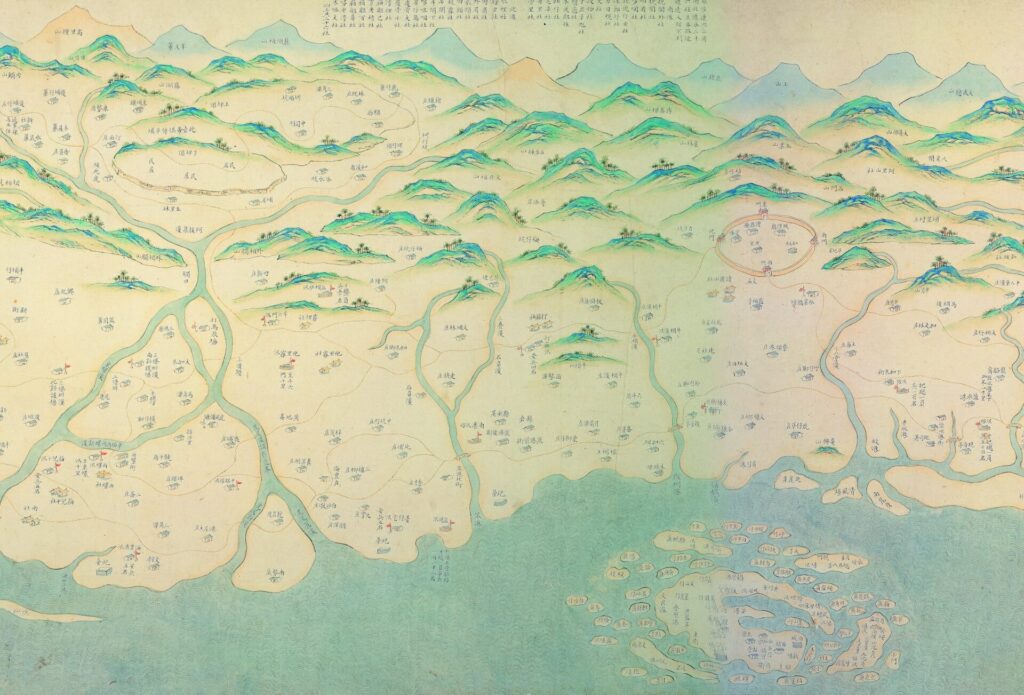
其中有云:
「蠻雲黯黯海天昏,冷對春燈憶夢痕。今月縱明輸古月,更無人說奪崑崙。」
在這個被厚重雲層障蔽了明月的元宵夜,丘逢甲備感寒冷,不禁也追憶起那格外光潔的故鄉明月,想著縱使今日廣東的明月高懸,那也比不上往昔在臺灣所感受到的元宵月色,從而慨嘆奪回臺灣幾乎毫無可能,蒼茫悲涼之意不難想見。
不過,因為「古月」又是「胡」字的隱語,所以「今月縱明輸古月」一句,還有「就算故鄉明月高懸,那也成了夷狄的明月」這層意思。
這兩層含意,都一再體現出丘逢甲對奪回故土臺灣的深切渴望。
無論如何,多元的修辭手法必須依據主體情志的需要加以活用,才能在豐富的內涵中,刻畫出獨樹一幟的自我,乃至於自身對社會的觀察。
在時、空座標中的「我」
無論是古典詩的鑑賞還是創作,「豐富的層次變化」、「有意思和趣味的內涵」,其實都是為了凸顯「我」在時、空座標中那獨一無二的位置,也因此能透過詩,展現出身處於那個時代之「我」的個性和思想。
不妨再以清末臺灣仕紳林維朝的〈博覽會場夜景〉一詩為例,林維朝歷經乙未割臺的創痛,始終皆以維護漢文化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,但也由於日本的殖民統治,使之意識到科技興邦的必要。
而這首詩正是寫於西元1907年,林維朝赴日參觀「東京勸業博覽會」之時,詩云:
「銀花火樹照輝煌,嘹喨仙音透碧空。到處嫦娥看逐隊,恍然身到廣寒宮。」
乍看之下,這首詩毫無新意,只是將所感受到的博覽會場比擬為仙境而已,傳統文士實不乏此類詩作!
不過,若進一步結合林維朝所處時代語境,就會發現這首詩並不是以仙境想像為根本旨趣。關鍵在於當時臺灣社會的電燈普及率極低,電燈主要仍使用於政府機關,至十年、二十年後,電燈的普及率才逐步上升。
所以這首詩的破題之句「銀花火樹照輝煌」,乃貫串全詩的樞紐,體現出了對科技的驚嘆,訝異電燈竟能令偌大的會場宛如白晝一般,故能欣賞歌舞表演,從而產生飄然飛昇月宮的錯覺。於是可以看到「我」在這首詩中,被明晰地標示在了一組特殊的時、空座標上,這首詩也就變得有意思了!

儘管詩之優劣的評判存在著「詩觀」差異,因而產生見仁見智的疑慮。但大抵而言,詩之優劣仍舊具有總體的評判原則:「豐富的層次變化」、「有意思和趣味的內涵」。具體來說,古典詩應以「立意新穎」、「意溢於言表」、「多重含意」為目標,並且能靈活運用多元的修辭手法彰顯主體情志,明確那個在時、空座標中的「我」。那麼,便足以確認這首詩是在一定水平之上的作品,也將不再人云亦云了!
林佑澤 博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