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一園子的燦爛需要百花齊放;曾經以四大發明,締造人類史上重要文明成果的中國,為什麼時至今日卻比不上西方的科技、繁榮與進步?先秦諸子中曇花一現的名家論辯,可以說是無謂之辯嗎?精確辨析,就是吹毛求疵、錙銖必較,或意氣相勝、口舌爭鋒嗎?主流應該凌駕一切發展嗎?生命哲學、知識論、管理哲學應該有區別待遇嗎?
歷史是一面鏡子,借古可以鑑今戒後,關於兼容並包的問題,很值得我們深思。
公孫龍(公元前320-25年)是戰國時趙人(今河北邯鄲),他和惠施一樣,都是名家的代表人物。他的「白馬非馬」論風靡一時,名、實之辨極其精彩。

惜乎後人對他的認識不多。不但如此,即連他的著作《公孫龍子》十四篇也僅存六篇,保存在明代的《道藏》中。
「名、實之辨」常被扣上詭辯罪名的帽子
人們厭棄「假」,虛假的情感、說法,使人打從心底反感,可是人們往往不懂如何覈實、不會求真?導致我們常被名實不符的情境所包圍。
名實不符譬如:口說愛民,卻將百姓驅赴戰場;宣稱護衛百姓財產,卻把良田作為戰場;說要請你吃好吃的食物、要介紹美麗(英俊)的人給你認識,或者宣稱某人「學問很好」、「能力卓越」……,結果卻並非如此,你會不會因巨大落差而失望?

那麼我們還能人云亦云地說,辨明「名、實」只是詭辯嗎?我國歷史上,誰最早且最用力於此?則公孫龍可以當之無愧。他從認識論的形上學角度,建構出「名」、「實」必須相對應的系統理論,論述名言概念必須與事實相符。可是先知往往是寂寞的。
以下先模擬一個說明「何謂名、實?」的故事:
一個狡詐的客人進飯館先點了一碗要價一百元的牛肉麵。坐下,他隨即說:「排骨麵也是一百元,那我不要牛肉麵了,可以改換排骨麵嗎?」老闆給他方便,就換成排骨麵了。吃完麵,他沒付錢就走了。夥計攔下他,請他付排骨麵的錢。
客人反問:「我為什麼要付錢?我是用牛肉麵換的啊!」
夥計於是說:「那就付牛肉麵的錢。」
客人又說:「我已經把牛肉麵還給你們了。我沒吃牛肉麵,為什麼卻要付牛肉麵的錢?」
客人言似是而非。「牛肉麵」在此是虛「名」,不是真實存在,即無其「實」;以牛肉麵之「名」,換排骨麵之「實」,就是「以名亂實」了——現實生活中,很多人正坐此盲點,以為有了名聲,就真是如此了;殊不知「名」不等於「實」,——「天下之所『無』」的「名」,不等於「天下之所『有』」的「實」,不要擔了個虛名,就自以為飛天了。
公孫龍曾經請出孔子為「白馬非馬」論背書
接著說戰國時期公孫龍提出了著名的「白馬非馬」論,但由於受到太多非議,他於是擡出春秋時赫赫有名的孔子來為他背書。
(問)「白馬非馬,可乎?」曰:「可。」(問)曰:「何哉?」
曰:「馬者所以命形也。白者所以命色也。命色形非命形也,故曰白馬非馬。」
(問)曰:「有白馬,不可謂無馬也。不可謂無馬者,非馬也?有白馬為有馬。白之非馬,何也?」
曰:「求『馬』,『黃』、『黑』馬皆可致。求『白馬』,『黃』、『黑』馬不可致。使白馬乃馬也,是所求一也。所求一者,白者不異馬也。所求不異,如『黃』、『黑』馬有『可』有『不可』,何也?可與不可其相非,明。故『黃』、『黑』馬一也,而可以應有馬,而不可以應有白馬,是白馬之非馬,審矣!」
(問)曰:「以馬之有色為非馬,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。天下無馬,可乎?」
曰:「馬固有色,故有白馬。使馬無色,有馬如已耳,安取白馬?故『白』者非『馬』也。 『白馬』者,『馬與白』也,『白與馬』也,故曰:白馬非馬也。」
公孫龍善辯,所以在戰國時,各家雖然抨擊「白馬非馬」論,認為是「詭辯」,卻很難在辯論中占上風。另一廂的公孫龍,則也很想把「理」說得服人心口,所書《公孫龍子》於是請出了孔老夫子:

《孔子家語》中有一段「楚王喪弓」的記載——楚王帶著名弓「繁弱」和名矢「忘歸」去雲夢澤打獵,而在狩獵中遺失了名弓,左右之人趕忙尋找。楚王卻說:「楚人遺弓,楚人得之,又何求乎?」他說反正最後會被楚人尋獲,就不必找了罷!孔子得知後便說:楚王若言「人亡之,人得之」,豈不更好!何必一定是楚人得到呢!
於此,《公孫龍子》正是藉故事中的孔子認為「楚人」和「人」不同,其「名/實」有異,以說明名言概念和對境有一種對應關係,「人」除了「楚人」外,還包括秦、齊、燕、韓……人。同理,「馬」除了白馬以外,也還有很多他色之馬,「白馬」對「馬」而言,是無法周徧論述的。所以他得意地說;「『白馬非馬』,乃仲尼之所取。」
「白馬」到底「是/不是」馬?——不對啦!公孫龍不是說屬性
兩造辯論,對方辯者係從「白馬」到底「是/不是」馬切入。當然,若從馬的屬性、種類言,「白馬」自然「是」馬類。
但問題是:公孫龍的邏輯範疇不是說馬的屬性,而是說名謂。所以當辯者以「有白馬,不可謂無馬」駁斥他時,他們其實並沒有對焦。
公孫龍強調的是,要從「白馬」的名言概念談對應,單說「馬」和冠以白色特稱的「白馬」不同。
也就是說「形名」的「馬」類,和「形名」+「色名」的「白馬」,是兩種不同的內涵。當有黃、黑馬時,只能說「有『馬』」而不能說「有『白馬』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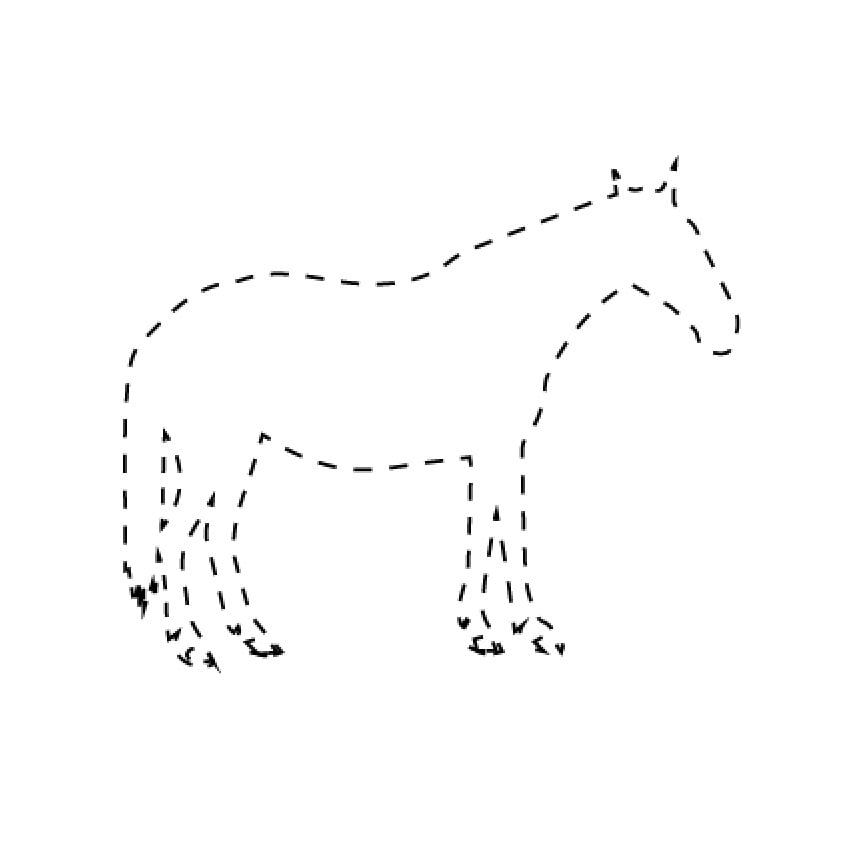

我們也可以從「全稱/特稱」的「通稱/專名」、「共名/別名」來理解「『白馬』非『馬』」論,便可知「馬/白馬」實不能混為一談。
荀子也曾說:「單足以喻則單,單不足以喻則兼。」如果「單名」能夠完整定義的,就用「單名」;「單名」不能完整定義的,就用「複名」。
此外,墨家的《墨經》亦嘗以「達、類、私」之名謂,區別邏輯範疇的「普遍/特殊/個別」範疇,故也有「殺盜非殺人」的說法:
車,木也;乘車,非乘木也。
船,木也;入船,非入木也。
盜,人也;多盜,非多人也,無盜,非無人也。
奚以明之?惡多盜,非惡多人也,欲無盜,非欲無人也。
《墨經》說車船雖然是木類所造,但是木類也可以造作木屋、門窗、桌椅……,所以木類的範疇大於車船,車船對木類而言並不周徧。因此不能把乘車說成「乘木」、入船說成「入木」。
先說完了一般人比較容易認同的說法後,緊接著,便說「盜」屬於人類,但是人是「大類名」,盜是「小類名」,人包含盜,盜卻非人的全部,除了「盜」以外,人還包涵「非盜」,所以盜不能作為範疇較大的人的通稱或通名。
於此,便可以推出並證成「不愛盜,非不愛人」、「殺盜,非殺人」的命題了。
(文章未完,待續請詳下篇 :「白馬非馬」不是公孫龍的最愛)
張麗珠 教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