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「讀〈出師表〉不哭者不忠,讀〈陳情表〉不哭者不孝,讀〈祭十二郎文〉不哭者不慈。」如果說〈出師表〉是忠的極致,〈陳情表〉是孝的極致,那麼〈祭十二郎文〉,就是慈愛的極致。
慈,從父母對子女的憐惜出發,也延伸到長輩對晚輩、兄長對弟弟、叔伯對侄兒的疼愛。這篇文章是韓愈寫給姪子韓老成的祭文,他的痛,從失去親人開始,一路延伸到血脈中斷、唯一依靠崩塌的深處。這份「血緣裡的哀傷」,本來就比文字更深。我們之所以能聽見他的心頭血汨汨而流,是因為這篇文章是寫給一個人的,不加掩飾的愛與悔恨,本身就是一顆心碎裂時必然發出的聲音。
孤苦人生裡的唯一依靠
「嗚呼!」雖是祭文的套語,但也是韓愈把千言萬語化作一聲的悲鳴,回望自己的生命,首先感受到的就是「孤」字。
父母先後離世,他幾乎沒享受過片刻的依靠,只能靠兄嫂照拂。熟料還能托付的兄長也客死南方。那時候,他和年幼的十二郎,就像兩個失根的小苗,一同跟隨嫂子歸葬河陽,又一起漂泊到江南討生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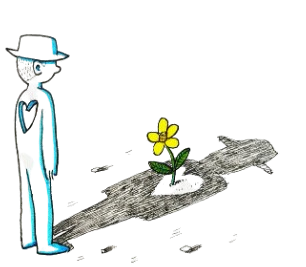
「零丁孤苦,未嘗一日相離。」這句話寫得直白,卻是最深的親情羈絆。只剩彼此,他們既不得不相依,也因此相依得更深。
韓愈其實有三個兄長,但一個個早早離去。到最後,能承接祖先香火的,只剩下侄輩的十二郎;能延續子輩責任的,只剩下自己。兩代人竟然只剩下兩個人。
「兩世一身,形單影隻」。那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呢?就像站在巨大的空廳裡,聽到自己的腳步聲孤零零地迴盪。整個韓氏家族的未來,被壓縮成兩個身影。
有一次,嫂子抱著小小的十二郎,指著韓愈說:「韓氏兩世,惟此而已!」

對孩子來說,這只是大人說的一句話,他太小了,無法理解。對當時仍是少年韓愈來說,他聽見了,也能記得,但還不懂這句話背後的悲涼。
直到多年後,當十二郎離世,那一句話才像一道烙印,在韓愈心口燙得生疼。童年的他像風裡的小舟,四面皆是冷浪。與他年歲相近、同被命運催促長大的堂侄十二郎,便成了他僅存的同伴與牽繫。十二郎輩分上是他的姪子,但年紀更近於弟弟。送別姪子,連同童年時光裡最親密的存在,一起被帶走了。
嫂子抱著孩子、指向韓愈,其實是把一個家族的命運交到兩個少年的肩上。
對孩童而言,這句話沉重得近乎抽象,但對成人而言,卻是清晰的責任軸心。
錯過一次,再錯過一次
韓愈十九歲入京,開始仕途奔走。四年後回家探望,見到十二郎。再過四年,他回河陽省墳,又遇見十二郎送喪。那一次次的相逢,都像命運偶然丟下的碎片,短暫卻無法持久。
後來他佐董丞相於汴州,十二郎也專程來看他,但停留不過一年,便說要回去接妻兒;誰知翌年丞相去世,韓愈離開汴州,十二郎的歸期便此落空。再後來,他調任徐州,本想派人接十二郎來,自己卻又罷官離任,團聚再次泡影。
原本以為,未來還很長。

韓愈心裡其實盤算過:十二郎若繼續留在原來寄居之地,終究只是寄人籬下,不能長久。最好的打算,是等韓愈在任所成家安定,再把十二郎接過來。這就是他對未來的想像:一個安穩的家,一個可以久處的親情。於是暫時的別離,在他心中,反而像是為長久相聚而準備。
沒想到命運竟然做了最殘酷的反轉,以為青春還在,以為時間充裕,卻不料少者先亡,長者反存。「嗚呼!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!」
原想先把日子撐寬,再把親人接回來,完成「將成家而致汝」的願景,就是他在苦日子裡咬牙編織的唯一盼頭。誰知世事無常,原本緊抓的盼望,在一夕之間失去了著落。
韓愈痛到直言:「誠知其如此,萬乘之公相,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!」這是最沉痛的懺悔。如果早知十二郎會先走,就算有人給韓愈萬乘宰相的尊榮,韓愈也寧可放棄,不願離十二郎片刻。韓愈的悔,是一連串來不及:來不及把十二郎接到身邊,來不及多說幾句話,來不及再多守候一天,來不及守住最後的日子。這一層悔恨,是〈祭十二郎文〉裡最尖銳的一根針,刺得千年之後的讀者,仍不忍卒讀。
當天地忽然失序
去年,孟東野來訪時,韓愈曾寫信給十二郎,信裡這樣說:「我還不到四十歲,視力卻模糊了,頭髮蒼蒼,牙齒鬆動。想想那些叔父兄長,一個個健壯卻早逝,像我這樣衰弱的身體,又能活多久呢?我不能離開京城,十二郎你又不肯來,我怕有一天我突然死了,留下你獨自抱著無盡的悲傷。」這本來是寫給十二郎的警語,希望能早日團聚,卻沒想到,先離開的竟然是十二郎。

韓愈反覆質問:「少者怎會先死而長者存?強壯的怎會夭折而病弱的還活著?」「是真的嗎?是夢嗎?傳來的消息會不會是假的?」
但證據擺在面前:孟東野的書信、耿蘭的報告,都說十二郎已經離世。他想起「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?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?」這樣的人,怎麼會先走?
「天難測,神難明,理不可推,壽不可知。」這一句話裡,感慨已經承受不住重量,轉而成為對天地失序的吶喊。哭到極處,韓愈便開始質問。為何盛德的兄長早亡?為何純明的十二郎不克繼家?為何自己髮已蒼、齒已動,反而一再存全?悲痛在此一路加深,最後推向對世界秩序的震怒。生死的座次被顛倒,該先行的未先行,該承擔的被迫離席。
「理不可推,壽不可知。」他寫下這些話時,答案早已無從索求,只剩人間的無力被一一攤開:「天難測,神難明」是一種承認,一種投降,也是一種清醒。從此以後,他不再輕易以理安慰自己。
無從確定的細節

他看著自己:頭髮蒼蒼漸白,牙齒一顆顆脫落,血氣漸衰,志氣漸微,離死有多遠?「幾何不從汝而死也!」若有靈魂,他們或許很快就會再見;若死後無知,悲傷不過幾時,卻也將無窮期地消失在世間。
他想到十二郎的孩子才十歲,自己的孩子才五歲。連少壯都不能保,這些孩子又能否長大?他在問的,其實是對自己的責任、對家族延續的恐懼:這些小小孩提,會不會跟自己當年一樣,早早面對無依?
更讓人心碎的是連「死亡的日期」都模糊不清。十二郎生前曾寫信說自己得了軟腳病,韓愈當時不以為意,以為江南常見的小病,不曾擔心。如今卻要問:是不是這個病奪走了十二郎的生命?還是另有隱情?韓愈翻著信件日期:十二郎的信是六月十七日,東野說十二郎六月二日去世,耿蘭的報告卻沒有日期,是東野的使者沒問清楚?還是耿蘭沒寫?這些細節顯得荒謬又無力,像是對亡者的最後一絲拉扯,連確定日子這麼小的事,也做不到。
韓愈用一連串疑問、假設、時間錯置,寫出「不敢相信卻不得不接受」的心理狀態,這樣的反覆與錯置,讀來像修辭,其實是接到噩耗時,腦中翻騰失序的真實狀態。韓愈只能在「或然、或不然」的反覆中,愈想愈亂。即使確知十二郎已不在,仍下意識抓住一絲「或許有誤」的可能。
如果只是訛傳,那該多好?
最卑微的安排

韓愈派人帶著供品去弔祭,也去照料十二郎的孤兒和乳母。守得下去,就讓她們完成喪期;守不下去,就早早接回來。其他的奴婢,就留著守喪。若還有一絲力量,他還想「改葬,終葬汝於先人之兆」,讓侄兒歸於祖墳。這些都是他最後的補救,但無論怎麼安排,仍掩不住心底的缺口。
「汝病吾不知時,汝歿吾不知日;生不能相養以共居,歿不得撫汝以盡哀。」
這幾句,是全篇最讓人心碎的吶喊。生時,沒能同住照料;死時,沒能親眼送別。入殮時不在,安葬時也不在。韓愈只能把自己判為「不孝、不慈」。
「一在天之涯,一在地之角;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;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。」這是最孤絕的寫照。活著時,無法相伴;死後,連夢裡都無法相逢。那份斷裂,讓他只能向蒼天控訴:「彼蒼者天,曷其有極!」

餘生所求,不過如此
韓愈明白,自己再無心戀人世。他說,從此以後,願只求「數頃之田於伊、潁之上」,過餘下的歲月。最大的願望,不是功名,不是仕途,而是:「教吾子與汝子,幸其成;長吾女與汝女,待其嫁,如此而已!」兩家的兒子能平安長大,兩家的女兒能順利出嫁,這就是他在大痛之後,僅剩的卑微祈願。
文章的最後,韓愈寫下:「嗚呼!言有窮而情不可終,汝其知也邪?其不知也邪?嗚呼哀哉!尚饗!」文字可以停下來,情感卻沒有盡頭,如決堤之水,無法收束。
在〈陳情表〉裡,李密告訴我們:幸福就是陪伴;在〈祭十二郎文〉裡,韓愈告訴我們:最大的痛苦,就是「來不及」。「祭文」的文體不過是它的外殼;在殼裡迴盪的,始終是血脈斷絕的恐懼、命運無常的質問,以及對「來不及」的深切懊悔。
這篇文章因此被反覆召喚,只為提醒我們:別把重要的人,留待「以後」。
黃承達 老師
